这季节向来不缺雨水。新下了一场雨,天才稍稍放了晴,很快又是沉沉的一片压下来,只从云层里透出一点稀薄的微白的光。田埂头一棵老杏花树,数日前还开得如冰绡暖云一般,现今花已落尽了,单剩下一地乱红碎雪,被碾得有些零落,倒叫人看了不免唏嘘一番。
唐嘉禾立在树下,蹙着眉盯着面前湿泞的泥土。有眼乖的侍从看出些许端倪,忙凑上前来讨巧,问是否要唤那女子过来。唐嘉禾摆摆手,解下织锦披风丢给近侍,便是下定决心般径直踏上了田间土路。近侍深知这大小姐的脾气,也不敢拦她,只好苦笑着捧了披风跟上去。
新雨初霁,田间小道松软湿滑,偏唐嘉禾走得又快,近侍在后边看得胆战心惊,生怕她一个不留神摔进地里去。好在那女子离得不算太远,唐嘉禾很快到了她面前,有些居高临下地望着她。
“别南燕,就是你?”
面前的女子只顾低头除草,恍若未闻。
“我认得你,四年前家父寿宴上,你师父带着你,”唐嘉禾轻呵了一声,语气微含讥诮,“当年你是空前绝后的亲传女弟子,如今也不过当了个村妇。”
“……”
“你家大师兄昨晚可是死了,在你们的正殿上,被人捅了个对穿,”别南燕终于直起腰来,转头看了她一眼,唐嘉禾不理会,自顾自说下去,“剩下的不过是群扶不上墙的,你回去,我就能让你坐稳掌门的位子。”
“我不认识你。”
“碧影山庄唐同甫,正是家父。”
“我认识你爹。”
唐嘉禾扬一扬下颌,“唐嘉禾,你最好记清楚,不久之后,你会经常听到这个名字。”
“你还没有报价,这必须是笔好买卖。”
“三个月后庆阳城,家父会登上武林盟主之位。”
清明细雨,草长莺飞,又是一年仲春。
庆阳城并不依山傍水,但唐嘉禾顶着武林盟主掌珠的名头,自然是不缺上赶着巴结的人。莫说在城里建个山林,便是她想要把蓬莱搬进庆阳城里,也不会有谁敢说个不字。有唐家大小姐的意思在,工匠们不敢怠慢,加之这掌门据说也是个不显山露水的高手,更是得罪不起的主。匠人卖力,辟翊门的重建堪称一日千里,落成那日唐嘉禾拉别南燕去看,疏朗朗一派俯水临流的秀丽景致,虽不似旧日山门峥嵘崔嵬,却是未曾见过的清幽旷雅,直叫别南燕看得呆了,直到唐嘉禾不耐地推她才反应过来,堪堪端住了掌门风度。
“……工匠是从江南寻来的名匠,用的最好的料子,下了十足十的工夫,”唐嘉禾领着别南燕一处处看过,眉目间颇有得色,“便是那些南方门派,也没几个敢说自家就比这处园子好的……”
辟翊门的弟子是认得唐嘉禾的,见了她恭恭敬敬唤一声唐大小姐,便引她去见掌门。一路分花拂柳,转过一座工巧亭台,绕过几处小小院落,果然见别南燕在一棵老杏花树下。那弟子打了个躬,径自去了。
这一日的天色极好,恰是骤雨初歇,天朗气清,薰暖的风徐徐吹过,卷落一树的胭脂粉雪。唐嘉禾眯了眯眼,一眼瞥见别南燕手里捧的一管白玉洞箫,忽地起了兴致,“你会吹箫?”
“……不会。”
“我学过一段时日,倒是偶尔吹来消遣。”
“……”
“你且拿来,我吹一曲你听。”
于是变成两人立在树下,别南燕呆呆地仰头望着满树杏花,听唐嘉禾吹一曲“何处玉箫天似水,琼花一夜白如冰”。
唐嘉禾的箫声并不十分精妙,大约如她自己所说的,真的只是“学过一段时日”而已。明明是有些清愁的歌词,她奏来却是水乡小调一般的轻软明快,平添了一分娇憨之气。
她吹不出愁肠百结倒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唐嘉禾的世界里从来没有“愁”字的位置,反正季春过了就是孟夏,杏花落了还有荷花,这世上从不缺桃李春风,她又何必拘泥于一处红衰翠减。有那伤春悲秋的闲工夫,戏台子上的戏都唱完几折了,不如快快活活地过她大小姐的日子罢。
一曲终末,唐嘉禾把箫递还给别南燕,又取出一张描金请柬来,“五日后便是我生辰,我爹要在碧影山庄办酒。你得来,”她看别南燕依旧是管自出神的模样,提高了些声气,“现在武林上人人皆知辟翊门同碧影山庄交好,你这掌门不来,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。”
红底金箔的请柬在日光下烁烁地亮,浓墨端楷的字被这底色一托,竟也耀目了起来,灼灼地似要印进人心里去一般。
“我会去的。”她说。
现在可是又一张大红请柬放在案上了。泥金薄缕鸳鸯成双红笺的请柬,金线细细勾勒了凤凰的纹样,里头也是浓墨的端楷,不过可不再是寿宴的请柬,而是婚宴了。
“阿禾与我下月便要成亲了,这帖子你得收着。”
是个不认识的男子,他口中的“阿禾”她倒认得的。
唐嘉禾给她看过合婚庚帖,那样喜艳的红色,衬得她整个人都添了一层喜悦的娇艳。
“两姓联姻,一堂缔约。良缘永结,匹配同称。看此日桃花灼灼,宜室宜家;卜他年瓜瓞绵绵,尔昌尔炽……”
正红蹙金绣云霞翟纹的霞帔。那彩翟锦绣团簇,靡丽飞扬仿佛要活过来一般。
烛影良宵。才子佳人。天造地设。话本子写得熟透了的。
只她是个旁人罢了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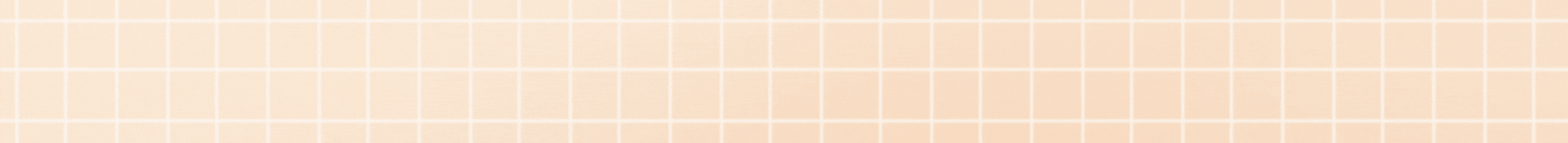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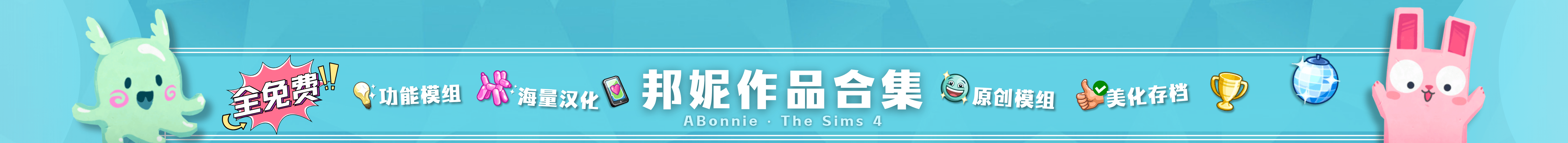


 提升卡
提升卡 解锁卡
解锁卡 千斤顶
千斤顶 擎天顶
擎天顶 微信扫码分享
微信扫码分享



 发表于 2021-5-4 13:52:08
发表于 2021-5-4 13:52:08
















 提升卡
提升卡 解锁卡
解锁卡 千斤顶
千斤顶

 ,赞美唐嘉禾大美女(哭
,赞美唐嘉禾大美女(哭





 客服
客服 微信
微信